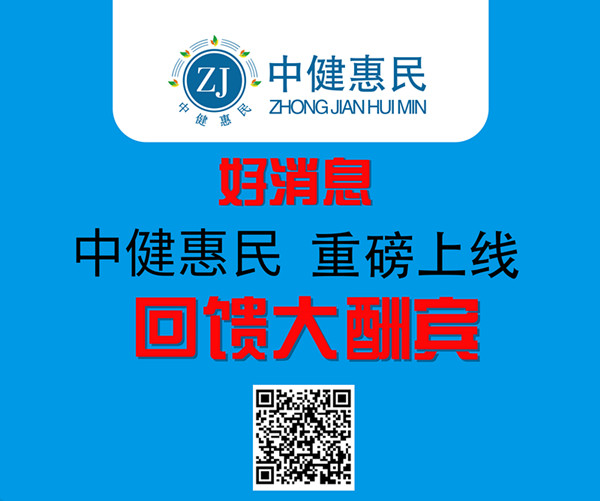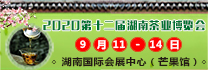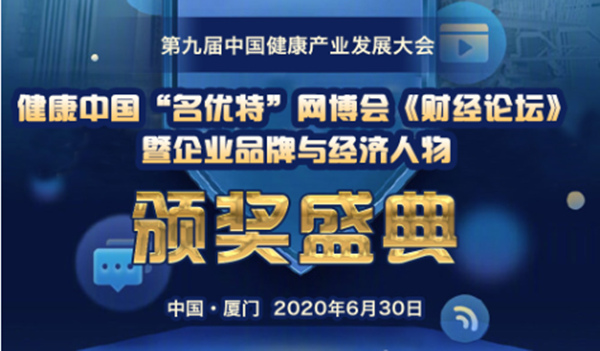有人说,爱情像茶,初尝是苦,回甘是甜,最后寡淡如水,却离不开了。
我不信,直到我遇见她——在一场“盲品”茶会上。
那天,我们被随机分到同一桌。桌上五款茶,只能看汤色、闻香气、尝滋味,猜产地与年份。她端起第一杯,抿一口就写下:“2018年,福鼎管阳,日晒牡丹。”我嗤笑:怎么可能这么准?结果公布,全中。我从此记住她——那个用“味觉”说话的女孩。
后来我们约会,从茶开始,也由茶结束。
原来,爱情真的有三杯茶。
第一杯:绿茶,把“喜欢”泡得轻一点第一次单独见面,她带了一罐恩施玉露。
玻璃杯里,针形茶叶垂直下沉,像一场安静的“跳伞”。她说:“绿茶要降温,80℃就好,太烫会把嫩芽‘烫熟’,苦得委屈。”
我故意问:“那爱情呢?”
她看我一眼,把水壶递给我:“先晾一晾,再碰。”
那一刻,我懂了:
绿茶式的喜欢,是“试探”——
谁也不敢用沸水般的热烈,怕惊到对方,只好把温度调到“刚好不烫手”。
我们聊茶,也聊童年。她说小时候外婆用搪瓷缸泡“老干烘”,一喝一下午;我说我爸把铁观音当“解酒药”,越浓越管用。
两代人的茶,两个世界的人,就这样在80℃的水里,慢慢舒展。
第二杯:单丛,把“热恋”冲得狂一点确定关系那天,她送我一罐蜜兰香。
凤凰单丛,以“高香”闻名,一揭盖,花香果香蜜香像烟花在客厅炸开。
我嫌味重,她却笑:“要的就是这股‘冲’,像喜欢,藏得住吗?”
于是,我们学会用盖碗“快冲快出”:
水即开即冲,前五泡5秒、10秒、15秒……
茶汤从金黄到橙红,香气由蜜兰转栀子再转杏仁,每一泡都是新的她——
会调香的她,把茶做成冰淇淋;
会拍照的她,记录茶叶从卷曲到伸直的24秒延时;
会吵架的她,摔过我最爱的建盏,又连夜用金缮“缝”回去,说:“缝好了,比原来还好看。”
单丛的“高香”,是热恋的“高音”,
哪怕邻居投诉“你们凌晨两点还在喝茶?”,
我们也要把最后一泡冲完——
因为知道,香再高,也会落;
人再热,也会冷。
但至少今夜,我们让花炸到极盛。
第三杯:普洱,把“余生”煮得慢一点在一起第三年,我们搬进一间老破小。
厨房小得只容得下一口电陶炉,她却开心:“正好煮普洱。”
那是2006年的熟砖,深栗色,像一块被时间踩实的泥土。
我们没盖碗、没公道杯,就用搪瓷锅煮:
先醒茶,再小火20分钟,茶汤稠得像黑巧,喝一口,舌苔被“糯”住。
她窝在沙发里织围巾,说:“熟普最好放,不怕闷,不怕煮,越煮越甜。”
我补一句:“也不怕吵,吵完还能一起喝。”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:
绿茶的“鲜”、单丛的“香”,都会过期;
只有普洱的“陈”,能把“我们”变成“咱们”。
它允许你犯错——
水加多了,多煮5分钟;
火大了,苦就苦,下一泡再降;
就像感情,
吵架把话说绝,夜里还知道摸黑找对方的手;
把“分手”说成口头禅,却记得对方胃不好,早上仍煮一壶熟普,兑牛奶,做成“茶拿铁”放保温杯。
尾声:茶会凉,但壶别收今年春天,我们回武夷山办“茶婚礼”。
没有司仪,没有誓言,
只在茶席两边摆了三个杯子:
一杯绿茶,敬相遇;
一杯单丛,敬相爱;
一杯普洱,敬相守。
来的人都以为是“仪式”,
只有我们知道:
那是把爱情泡成日常——
苦归苦,甜归甜,
最后都变成身体里的“体温”,
摸不到,却离不开了。
所以,
如果你问我爱情像什么?
我会先烧水,
然后答:
“像茶,别怕冷,
凉了,就再冲一泡。”